作者:李超
來源:稜鏡·騰訊小滿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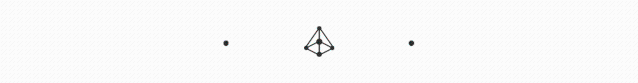
編者按:
2019,與君越過山丘;2020,笑對滾滾紅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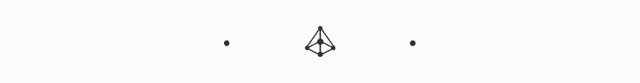
2019年,對於那些生活在A股“森林”中的“動物們”來説,五味雜陳。
這是收穫的季節。
豬肉價格提升讓生豬養殖公司牧原股份(002714.SZ)一飛沖天,股價年內上漲4倍,創始人家族更是在內地企業家財富榜上“反殺”王健林和雷軍等一眾大佬,由去年的第68位躍升至第9位,成為許家印後第二個進入榜單前十的河南籍富豪。依靠牧原豬,公司高管們在年內的減持金額更是超過50億元。
這是迷茫的季節。
獐子島(002069.SZ)的扇貝在年底又“消失”了,這是它們繼2014年和2018年後的第三次意外死亡。獐子貝“寧死不屈”,高管卻在期間減持,其中董事長吳厚剛減持額過億。實際上,證監會在今年年中才剛剛對前次扇貝死亡事件做出處罰決定:因信批違規和涉嫌財務造假,包括獐子島董事長在內的涉事人員被禁入證券市場。“涉嫌”二字,結合扇貝再度死亡,讓劇情更加懸疑。
這還是奔放的季節。
3年前四川雙馬(000935.SZ)連續37個交易日19個漲停板,成為史上最大妖股之一;今年,奧馬電器(002668.SZ)將當初14億元從大股東手中收購的互聯網金融資產,以2元“白菜價”賣還給了大股東,“脱韁野馬”的資本運作在互金政策收緊下“馬失前蹄”。
全聚德的鴨,七匹狼的“裝”,還有那躲不掉的“黑天鵝”與“牛熊”,和人類社會一樣,A股“動物世界”裏,本沒有新鮮事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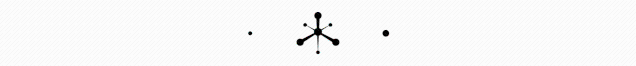
河南新首富碾壓雷軍王健林
“你們今年養豬賺了多少錢?”年底的中國企業領袖峯會上,王石問新希望(000876.SZ)董事長劉永好。
“我們今年的效益不錯,請你吃飯一點問題沒有,吃豬肉。”劉永好笑答。
2019年A股最有“錢途”動物,無疑是“二師兄”。隨着豬價年內大漲,養豬上市公司紛紛爆發,新希望市值由年初的300億上升至800億,温氏股份(300498.SZ)最高漲幅70%,而其中風頭最勁的,當屬牧原股份——其股價由年初的28元/股扶搖而上,在10月底一度超過100元/股,十個月上漲4倍,市值超過2100億元。
這波行情,也讓牧原股份創始人、向來低調隱祕的河南“豬倌”秦英林出現在公眾視野。在11月最新公佈的福布斯內地富豪榜上,秦英林家族以1174億元財富值躍居第9位,反超了包括王健林(884億)、孫宏斌(707億)、雷軍(615億)、張近東(587億)和張一鳴(1146億)等在內的來自互聯網、地產和零售行業的大佬,刷新了河南本土企業家在福布斯的最高排名,取代天瑞集團李留法成為新任河南首富。
去年,秦英林家族還僅以245億元排名第68位。
在這輪豬價起飛前,關於秦英林的公開報道並不多見,只知道,農村出身的他17歲便因家中僅有的20頭豬死於瘟疫而開始鑽研養殖,畢業於河南農業大學畜牧專業;同時,秦英林還是“92派”一員。招股説明書顯示,現年54歲的秦英林於1992年辭去國企工作,與畢業於鄭州牧工高專獸醫專業的妻子錢瑛回到老家河南內鄉,“下海”創立牧原,從22頭生豬起家,用了22年時間,於2014年以60億元估值在A股完成IPO。2017年,秦英林曾將60輛奔馳轎車作為福利發放給員工。
牧原股份在2019年不僅實踐了“養豬致富”,而且證明了與資本合璧還可以“鉅富”。同在財富榜上表現相近的是,牧原股份在今年A股減持榜上也高居前五。
12月10日,牧原股份公告表示,公司第一期員工持股計劃全部出售完畢。該計劃於2015年底推出,彼時以30.42元/股的認購價共發行2235萬股股份,鎖定期至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開始,已經解鎖並經兩次高送轉變為8047萬股的持股計劃開始減持。根據choice數據,以牧原今年60元/股均價計算,這份當年6.8億元的投資保守估計變現53億元,三年多時間增長7倍。
秦英林帶動了家族和鄉親的共同富裕,但其本人的減持卻遭遇“血虧”。2016 年,秦英林夫婦全資持有的牧原股份第二大股東牧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發行可轉債,該筆可轉債在今年完成換股7674萬股。按照約定,“債主們”的行權價僅為13元/股左右,秦英林夫婦被動套現10億元。該筆股份按照今年股價,對應市值可達50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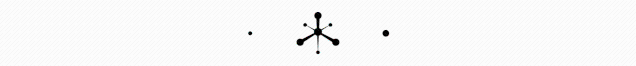
“瘋狂”週期催肥牧原豬
實際上,牧原股份在今年一季度淨利潤還處於-5.4億、同比下降500%的鉅虧狀態,而從2014年到2018年,其有兩個財年淨利潤同比降幅超過70%。作為典型的週期性行業,豬肉股並不總是如此“值錢”。
“豬週期”通常為三到四年。根據牧原股份招股説明書,我國生豬養殖行業集中度較低,例如在2011年50頭以下養殖户就達到5500萬,每户數量變動一頭,總供給量就會產生10%波動。當豬價高企時,養豬積極性增加,但從繁殖種豬到商品豬最終出欄,需要1年半左右時間,滯後性導致新增產能落地時,市場已經供過於求,豬價隨之在又一個1年半時間裏持續下跌,最終大批農户退出市場、供給減少,豬肉價格再次上升,形成周期。
上一輪豬週期的高點出現在2016年,前後兩個低點分別為2014年和2018年,這兩年也正是牧原股份業績的低谷時期,淨利潤分別僅為4900萬元和4.6億元,而中間三年(2015-2017年)豬價上升期,淨利潤分別達到了5.7億元、23億元和24億元。
疫病作為偶發因素,也對“豬週期”產生影響。去年上半年,豬價從低點開始新一輪週期增長,但8月份豬瘟的發生打破了節奏,並在今年疫情穩定後最終加劇了供需關係的緊張和豬價上升週期的恢復。
按照劉永好的説法,今年10月份,國內生豬存欄量已經只有往年的40%。這直接催生了業績,財報顯示,今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牧原股份單季度淨利潤分別達到3.9億元和15.4億元,三季度同比和環比分別增長260%和300%。
實際上,豬肉價格波動屬於一種相對正常的行業現象,而為了減小波動,國家一直在通過政策補貼、扶持規模化養殖、投放儲備豬肉、防災防疫和加強流通渠道管理等多項舉措規範市場、穩定豬價。
根據國盛證券研報,2007年我國生豬年出欄量在1-49頭的養殖比重為48.70%,2015年下降為27.5%;出欄5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比重從2007年的26%上升至 2015 年的 43.2%。2016年,農業部發布《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明確提出了2020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比例要從 2014 年的42%提升至52%。
財報顯示,全產業鏈自營的牧原股份生豬出欄量由2014年的186萬頭上升至2018年的1100萬頭,市場佔有率從0.25%提升至1.59%。而“公司+農户”模式的温氏股份市佔率為3.2%,前10大豬企市場份額由2017年的5%左右提升至8.6%。隨着行業集中度提升,起伏不定的“豬週期”有望被改變。
對於行業集中度和“豬週期”的變化,牧原股份對《稜鏡》表示,因為非洲豬瘟影響,目前行業供需缺口較大,對技術和資金上擁有優勢的大型企業來説確實增加了機遇,而以往“豬週期”經驗在目前特定環境下不適用。
在年末豬肉價格企穩並預期回落後,資本市場上持續半年的“豬瘋狂”也告一段落。10月底,股價進入巔峯的牧原股份開始進入下行趨勢,一個多月時間股價跌至80元/股,下降了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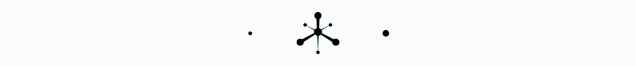
獐子貝在“死守”,股東們在減持
如果説“牧原豬”在2019年登上了A股“紅榜”,那麼“獐子貝”則再次因為“我命不由己”登上了“黑榜”。
11月,獐子島扇貝再度“消失”,其表示在秋季抽測中發現,2017年和2018年存量底播的蝦夷扇貝出現畝產大幅下降的情況,已構成重大存貨減值風險,預計將計提存貨準備2.8億元,佔該筆扇貝存貨賬面價值的90%。
這已是獐子貝第三次非正常死亡。2014年,獐子島因為扇貝遭遇冷水團“跑路”首次計提存貨減值2.8億元,而在2018年扇貝又因為營養不足“餓死”,再度計提減值6000萬元。實際上,在本次扇貝減產前,證監會剛剛公佈針對前次事件的調查和處罰結果。
證監會在7月公佈的處罰書顯示,根據第三方提供的捕撈軌跡圖,獐子島2018年的減值海域中,2015 年和2016 年底播蝦夷貝分別有 6.38 萬畝、0.13 萬畝已在以往年度採捕,致使虛增資產減值損失 1111萬元,佔減值金額的 18.29%。最終,包括董事長吳厚剛在內的相關涉事人員,以信披違規和涉嫌財務造假為由被採取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的措施。
“涉嫌”二字,讓最為核心的獐子島究竟是否造假問題,顯得更加撲朔迷離。斷定扇貝是人為造假還是自然死亡,已經超出了監管部門的能力範圍。
扇貝第三次折戟後,大連市農業農村局曾於11月16日組織專家調查組進入涉事海域,11月18日,其對外表示調查結果已上報,扇貝死亡確有其事,死亡原因複雜,需要進一步研究。但詳細調查結果至今尚未公佈。
獐子島前身為1992年成立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大連獐子島漁業總公司,股東為長海縣獐子島鎮人民政府和附近三個海島上的村民委員會,2006年A股上市,鎮長吳厚剛出任董事長並持有上市公司7.5%股份。
蝦夷扇貝曾經是獐子島的主打產品。招股説明書顯示,其擁有了這種以日本蝦夷族命名的扇貝的底播技術,即將貝苗投入到大海中讓其自然生長,從播種到收穫的週期在3年左右。相對於浮筏養殖,底播扇貝附加值更高且不受季節影響,同時並不存在“出逃”可能,因為蝦夷扇貝終身移動範圍不會超過25米。蝦夷扇貝底播技術,被獐子島稱為是自己最主要的優勢之一。
2009年和2010年是獐子島的巔峯,淨利潤增速分別達到65%和105%,股價創造了2年10倍的“奇蹟”。根據財報,2014年之前,蝦夷扇貝佔到獐子島利潤構成70%左右,而後出現斷崖式下跌,2018年已經下降至15%。
五年三次出現扇貝死亡,而如果把時間維度拉長,獐子島從2011年至今,底播的蝦夷扇貝幾乎全部出現過問題。
與“寧死不逃”的扇貝相比,獐子島股東高管則在同一時間通過二級市場密集減持。根據Choice數據,2014年之前,獐子島極少發生重要股東減持事件。2016年6月,獐子島大股東、由獐子島鎮人民政府控股的長海縣獐子島投資發展中心分兩次減持4700萬股,參考市值4.2億元;同年9月和10月,董事長吳厚剛又分兩次減持1000萬股,參考市值1.1億元;而在2017年12月,獐子島高管和員工參與的“和島一號”資管計劃分四次減持200萬股,參考市值1600萬元。
這些減持股份總共佔所有流通股不到9%的股份,在扇貝第二次死亡前套現5.4億元。而截至最新股價,獐子島目前總市值不過19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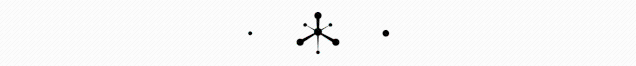
奧馬電器互金跨界鬧劇
在A股動物王國的奇葩故事裏,不僅有田間生豬和海遊扇貝,也從來不會缺少狂奔突進的“野馬”。
2016年,IDG的入主,讓股價長期萎靡的水泥公司四川雙馬(000935.SZ)連續37個交易日19次漲停,一騎絕塵;今年,冰箱製造商奧馬電器則因為互金淪為了“笑話”。
12月16日,奧馬電器公告表示,其準備將總共花費14億元收購的全資子公司“中融金”出售給實際控制人趙國棟,價格為人民幣2元。
這起鉅額差價的轉讓始於2015年10月。彼時,互聯網金融生機勃勃,奧馬電器以6.1億元現金收購自然人趙國棟所持有的“中融金”公司51%股權,同時,趙國棟以12億元購買原股東股份。變相借殼後,趙國棟成為奧馬電器新實控人,上市公司也從電冰箱跨界互金。
中融金在2015年和2016年完成了總共2億元的淨利潤業績承諾,於是2017年5月,奧馬電器再次以現金7.8億元,從大股東趙國棟手中收購中融金剩餘49%股權,並在同年2月,通過定增方式募資19億元建設互金項目。這起定增中,有8.8億元由趙國棟控制的融通眾金認購。又是一輪資本運作後,中融金成為奧馬電器全資子公司。
互金在此後的命運不用贅言,根據“2元”公告,因為金融政策和行業環境變化,2017年仍然能完成2.4億元業績承諾的中融金如今已經爛賬一片,截至今年三季度,其淨資產為-5.8億元、應收款13.5億;同時,因與渤海銀行業務糾紛,中融金股份還被凍結。正是這樣的背景下,趙國棟以2元的象徵價格將中融金回收。
2018年,中融金鉅虧8.5億元,根據業績補償協議,趙國棟將按照當時49%股權7.8億元對價為封頂進行業績補償,奧馬股份有4.7億元轉讓款未支付,趙國棟需要補回3.1億元現金;而2015年的6.1億元51%股權,由於完成了業績承諾,並未被提及。
換句話説,奧馬電器用6.1億元買到了中融金在2015年至2017年帶來的總共4.6億元賬面淨利潤和2018年8.5億元的賬面虧損,而上市公司表示,能夠最終追回趙國棟補償金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趙國棟則通過轉讓和定增總共花費20億元成為奧馬股份實控人,同時在2015年收穫6億元對價。
誰來為奧馬電器這筆歷時4年的“鬧劇”買單?
根據此前收購和定增公告,趙國棟資金來源多為自籌,但具體出處並未説明。同時,中融金旗下多個產品從事網絡借貸業務,誰是真正的“割肉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A股的動物叢林中,從來不會缺少“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