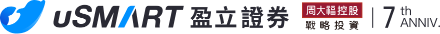於是13年後,令很多影人和影迷提起時都想倒吸一口涼氣的兩個名字——詹姆斯·卡梅隆,帶着他的《阿凡達2》回來了。
在他們“消失”的這13年裏,古老的好萊塢裏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顛覆:
先是凱文·費奇把漫威的視效大片拍成連續劇並取得空前成功,穿着各色披風與緊身衣的超級英雄很快擠滿所有檔期;
再是以奈飛爲首的流媒體在新冠紀元的年代大行其道,越龐大的連鎖院線越快破產。觀衆更願意躺在沙發而非走出家門買一張電影票,大製片廠們也優先把拷貝上傳網絡,而不是選擇寄送到放映員手中。
對這一切,“好萊塢編劇教父”羅伯特·麥基的預言是:到2050年,電影院就會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面對這麼個棘手的局面,卡梅隆,幾乎是最善於製造奇蹟的這位電影大師,和他手下最負盛名的電影系列回來了,之於這個死氣沉沉的、一蹶不振的、甚至行將就木的爛攤子而言。
這是一杯絕頂新鮮的juice。
01
人們對《阿凡達2》懷有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對前作在2009年冬天創造的那場震撼體驗念念不忘。
在用3D技術徹底革命傳統觀影方式的同時,《阿凡達》用27.9億美元票房刷新影史第一,意味着這部電影在商業意義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這種足以令任何一位導演垂名影史的神蹟,放在卡梅隆身上,實在算不得什麼驚天動地的成就。早在1997年,他執導的電影《泰坦尼克號》就在全球賺到18億美元票房,已經打破過影史紀錄。
更早之前的1984年,卡梅隆在自編自導的處女作《終結者》上映時,創造了以650萬美元成本換來7800萬美元票房的奇蹟。13年之前的《阿凡達》,只不過延續了卡梅隆從入行伊始保持的記錄:
每隔10年左右,就要更新一次自己親手寫下的票房神話。
今年的《阿凡達:水之道》在劇情上承接第一部末尾,時間線則推移到若幹年之後,前作的人類男主和納美族公主已經生兒育女。除了這對眷侶,地球人和納美族之間的戰爭仍未結束,貪婪的外鄉人和原住民之間註定無法和平共處,將繼續在戰火中演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單從預告片來看,《水之道》在技術表現力上又朝前邁了一大步。前作《阿凡達》處處透露着“飄逸”的概念,比如懸空漂浮的哈利路亞山,納美人騎着女妖在雲中穿梭。
如果《阿凡達》的主場是天空,《水之道》着重表現的場景則是“海底”。那裏更安全、更神祕,蘊藏着無限可能。水之道通往哪裏,暫且不得而知,但卡梅隆在採訪中說:
“我們開始突破電影的極限”。
對大師們而言,方寸之間的鏡頭是盛放想象力的最佳容器,甚至超過科學與文學。而插在想象力之上的那對翅膀,一隻叫故事,另一隻叫做技術。
《阿凡達》上映之時,最令人震撼的是在技術上的突破。然而13年過去,對卡梅隆和該系列IP而言,它更成功的地方應該是通過了時代的考驗。
即,在那層開創電影技術新紀元的濾鏡淡化後,這部電影依然被觀衆認爲是一個經典的好故事。
這就是IMAX 3D技術已經不再稀有的當下,《阿凡達:水之道》的預告片爲什麼仍有能力在全球範圍內激起熱烈反響。因爲它看起來是如此潛力十足,似乎已準備好了去創造下一個影史奇蹟。
02
有必要再聊聊卡梅隆。
如果潘多拉星球是一片世外桃源,卡梅隆就是這個未知世界的造物主,他的嚴謹和耐心賦予了這裏每一種植物和動物從形態到語言的驚人想象力,同時因爲生物和語言學家的背書而不失合理性。
卡梅隆一向熱衷於在虛擬世界中追求真實的體驗。拍攝《泰坦尼克號》時,他曾親自下水體驗了一番溺水的感覺,這纔在大熒幕上如此逼真地呈現出人類在世紀災難面前的絕望與窒息感。
在《水之道》裏,卡梅隆和他的團隊再次花重金打造了一艘潛水器潛入到馬裏亞納海溝的溝底,實地調查海底景觀爲這部電影尋找設計靈感。
卡梅隆本人始終追求在電影製作中探索數字科技的邊界,《阿凡達》對3D技術的引領無人能出其右,永久改革了電影呈現形式的潮流。但在將電影特效發揮到極致的同時,卡梅隆也一直在科幻片中不厭其煩地採用實景拍攝,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位大師的做派。
有趣的是,被稱爲“實拍狂魔”的諾蘭其實與卡梅隆分屬好萊塢水火不容的新舊兩派。在對電影技術的革新或守舊上,兩派導演在觀念上的衝突始終不曾停息。
保守派代表如諾蘭與昆汀,固守着實景拍攝與70mm膠片機。他們認爲天然的膠片顆粒賦予了電影畫面史詩般的厚重質感,膠片機獨有的飽滿色彩也令好萊塢先進的後期調色與CGI技術相形見絀。
激進派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則當屬斯皮爾伯格與卡梅隆,他們一向不吝於充當新技術的急先鋒。《侏羅紀公園》是好萊塢第一次把成敗賭在數字特效上,《頭號玩家》在觀影體驗上幾乎可以與《阿凡達》畫等號。
然而即便像斯皮爾伯格這種首屈一指的特效大師,在拍攝《大白鯊》時仍然堅持把攝影機放進大海而不是錄影棚裏的遊泳池,這與卡梅隆在《水之道》片場的做法如出一轍。於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這四位將電影商業性與藝術性結合得幾乎最好的導演,無論在技術上的執着有何不同,追求的都是畫面呈現在熒幕上的真實感。
而真實感,最終是在爲故事服務。人們走進電影院,燈光暗下,畫面亮起,電影無論在題材上貼近或者遠離現實,最終目的都是爲他們提供一段與真實生活不同的超凡體驗。
就像人類主角與阿凡達連接後陷入沉睡,然後睜開另一雙眼睛,觀看這個世界。
03
好萊塢似乎總在不厭其煩地折騰那些經典IP。
雖然這些翻拍與續集中不乏《銀翼殺手2049》與《瘋狂麥克斯4》之類傑作,但更多的還是狗尾續貂,例如食之無味的《黑客帝國4》,和正在路上的第10部《速度與激情》。
每當我們回憶起年少或年輕時的經歷,總會自動給它加上一層柔和的濾鏡。那是歲月的功勞,它讓傷痛不再劇烈,令快樂更加醇厚。一部精彩的電影,一次愉快的約會,無疑屬於後者。
這就是爲什麼老IP們的生命力如此旺盛,它們與一代人的記憶聯結,賣的不是電影票而是情懷。周星馳北上的幾部電影平平無奇票房卻不俗,與此同理。
在好萊塢的“黃金時代”,電影人信奉的是“爲藝術而藝術”。奧斯卡學院創始人、執掌八大之一米高梅的路易斯·梅耶曾說:
“我願雙膝跪地,親吻有才之人走過的地面”。
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梅耶對電影藝術的追求建立在對市場的把控上。“黃金時代”背後,是八大製片廠壟斷了全市場17%的院線和75%的電影產量,獨立電影人和院線淪爲附庸。
1948年,一紙《派拉蒙法案》宣告了大製片廠時代的終結。旱澇保收的日子遠去了,同時電視節目開始流行,媒體第二次喊出“電影已死”的口號(上一次是廣播節目的流行)。
製片廠死而不僵,從此進入大片時代,“用大片抗衡電視”的理念令電影院重獲生機。大片的定義從史詩、戰爭、科幻發展到如今的超級英雄系列,終於徵服全球,但也難以爲繼。
從2007年至2011年,好萊塢除迪士尼外五大製片廠總利潤下降了70%,總利潤只佔母公司個位數。2011年到2017年,北美佔全球票房比重從31%降到27%。疫情爆發前四年,北美年度票房分別是114、111、119和114億美元,市場增長陷入停滯。
直到疫情爆發後,北美票房驟降爲22億美元,奈飛當年營收幾乎是其10倍。院線紛紛破產,大製片廠宣佈進軍流媒體,人們再次想起了被“電影院已死”支配的恐懼。
寒冬給了行業充分的思考時間,是什麼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是疫情、奈飛、還是超英電影的流行。其實這些都是次要因素,好萊塢自身的墮落纔是它衰敗的最大原因。
大片時代高投入、長週期和高風險的製作模式使好萊塢變得固步自封,然而觀衆們審美水平的進化和好萊塢的流行是一對螺旋上升的矛盾,它們終有無法調和的一天。又長又臭的續集和無限翻拍不會總有人買賬,漫威的崛起實屬換湯不換藥,何況在後復聯時代也顯得乏力。
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好故事。不是所有文化都對穿着制服的肌肉男感冒,比如超英片始終未能徵服的日本市場。但殖民與反抗作爲近代全球歷史的主旋律,一定有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共鳴的歷史基礎。
這就是《阿凡達》在13年後仍然值得期待的原因。
04
世界聚焦於《阿凡達2》,並非只是期待什麼類似於IMAX的新玩意兒。4D、5D、搖晃、噴水、觸電,這些花活只是院線垂死掙扎的噱頭。
最終我們會發現,再先進的視聽技術也只能淪爲電影的佐料。被影史定義的偉大不是技術本身,而是一個純粹的好故事,這正是當代好萊塢最稀缺的。
就像卡梅隆自己所說:
“故事和情感永遠是第一位,而技術是次要的。我不會讓3D和高幀率這些技術問題影響到我故事的講述,極高的高幀率會讓電影看起來像普通的視頻,我不希望那樣。畢竟,那些都只是工具。”